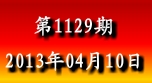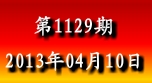感念母亲
感念母亲
■牛芳
母亲是位平凡的农村妇女,她十六岁就嫁给我的父亲,撑起这个家。那时家里人口多,衣服鞋子都是手工做,有多少个夜晚,当我在睡梦中睁开眼,就看到母亲在昏黄的油灯下做针线。所以尽管我们家孩子多,日子过得很艰难,可一年到头我们一家人,都穿戴整齐,这都得益于母亲的一双巧手:大人的衣服穿破了,修修剪剪,就成了我们可心的裤子,或衫子;膝盖磨破了,剪块小布丁,三针两线,就是一只兔子,或是一朵小花;我们脚上的鞋子,永远都是这双没穿破,新的就已经做好了。直到我的女儿小学毕业,都还穿着母亲改做的衣服,她还自豪地向同学炫耀,我的衣服是“外婆牌”的,独一无二的品牌。
不仅家人,就是全村,有多少人穿过母亲做的衣服,现在已记不大清了。但当时母亲给村人做衣服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快过年了,人们都在忙忙碌碌准备年货,给家里孩子做件新衣是最重要的,今天东家阿姨拿几块布料,来家里说,给我家二狗、三妮做件衫子和裤子;明天西家大婶也来了,说给她家毛蛋和狗剩做件中山装或红卫服......很快我家的炕头上,就堆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布料。母亲一手拿剪子,一手拿粉笔,画画剪剪,又踩着那架”蜜蜂牌”缝纫机,一顿饭的功夫,一件新衣服就好了。那堆花花绿绿的布料,在年三十之前,一律变成孩子们称心的衣服,而母亲得到的是村里人的千恩万谢。
母亲是个慈善的人,她有着菩萨一样的心肠。记得当时村里有一位五保的老头,无儿无女的,住在村里饲养室的窑洞里。常常是吃了上顿无下顿,母亲看他可怜,就经常做了饭让我们给他端过去一碗,还把爷爷穿过的衣服,收拾收拾给他穿。有一次,那老人病了,母亲拿出了舍不得吃的藕粉,给那老人喝,惹得我们眼馋了好长时间。后来,老人过世,身上的寿衣都是母亲和几位热心的阿姨给做的。
母亲虽然只有扫盲班的水平,但颖慧达理,在大事上不糊涂。直到现在我都感念母亲,她不但给了我生命,更给了我今天的生活,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一九七七年初,我高中毕业,像许多回乡青年一样,成了一位农民,那年我十六岁。母亲看着我瘦弱的身体在田间劳动,心如刀绞,但又无法摆脱这种境况。那时只有有门路,而且根正苗红的人,才有可能去城里工作,像我这“右派”的崽子,可教育好的子女,怎么有资格进工厂?不久,喜讯传来,高考制度恢复,改变命运的机会有了。一天,在田里锄地时,和母亲关系很好的阿姨问道:你想让娃在农村劳动一辈子吗?母亲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想,我做梦都想让我娃出去。可我没办法哇。那位阿姨说:那行,我给我当家的说说,让娃补习去,上大学。母亲拉住那阿姨的手,感激地说:好呀。几天后,我走进了学校,成了一名插班的补习生。要知道在当时母亲和我是顶着多大的压力呀,村里有人议论纷纷:多大的女子啦,不说找个下家嫁人,还去念书,想出去工作想疯了。我每次放学都躲着收工的人群,要不小心碰上了,有人会不阴不阳地说:呦,大学生,放学了!不管咋样,我有了重新上学的机会,心想,就是死也要考上大学,对得起母亲的希望。我如饥似渴,两头不见天,拼着命地学,终于如愿,考上了大学,跳出农门,有了可心的工作。要不是母亲当年英明果断的决定,能有我的今天吗?
正因了母亲的英明决定,我在考上大学的同时,也收获了爱情。但他家经济条件不好,听说还欠着千元的债,这在当时的农村可是个天文数字呀。记得当时给父母说这件事时,是夏天一个明亮的月夜,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土炕上,劳累一天的父母,躺在炕上听着我的叙说,我怕他们不答应,就尽量捡好的说,看我为难的样子,母亲一锤定音:“不说了,你看上的,我们同意,是沟是崖,你自己跳。人常说,好男儿不在家当,好女儿不在嫁妆。好好过日子,比啥都强。”我欣喜地看着父母,心里激动极了。银色的月光照着他们的面容,我看到,父母老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过好日子,孝敬他们。现在我的小家平安幸福,全是托父母的福呀。
母亲现在已经快八十了,身体很硬朗,还照看着小孙子呢。一天到晚还是忙忙碌碌的,不是操心这个,就是担忧那个,还是我们的大管家,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我们都得向她老人家请示汇报。母亲,是我们儿女的主心骨和精神支柱。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母亲是我们手心里永远的宝贝。我们永远感念您,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