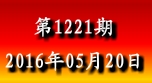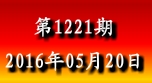受恩深处宜知退
受恩深处宜知退
□唐宝民
汉代有个叫疏广的人,从小喜欢学习,精通《春秋》等书,在家中讲学,名声特别大,被朝廷聘为博士、太中大夫,后来被提拔为少傅、太傅。他的侄儿疏受也很有才华,先是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后来也被提拔为少傅。于是,每当太子上朝时,总是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很是荣耀。五年以后,太子已经十二岁了,已经通晓了《论语》《孝经》,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少年了。这时,疏广便对侄儿说:“我听说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道理,‘功成身退’是老天教人这样做的,现在,我们叔侄二人已经做了二千石的官,身居高位,可是如此下去,难免会有后悔的事情发生啊,我们不如辞官回家养老,这不也是很好的事情吗?”疏受听了叔叔的话,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当天,他们叔侄两人就以有病为由向皇上请假三个月,皇上准许了。但三个月期满后,他们又以病情加重为由,要求退休,皇上挽留不住,只好准许了他们。于是,他们回到故乡怡养天年,全部寿终。疏广身处名利场中,却能保有一颗清醒的头脑,能看透官场的本质,懂得“受恩深处宜先退”道理,选择将名利轻轻放下,急流勇退,终得善终。
可是,并不是所有身处名利场中的人,都能对功名利禄参得透,比如,明代学者宋濂,虽然饱读诗书,却没能看清官场的水到底有多深,结果大祸临头,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宋濂本是一个书呆子,隐居于龙门山中,以著书为乐,闲时看看花、看看水,是一个十足的逍遥达人。然而,当朱元璋请他出山的时候,他却没能看破功名之累,感激涕零,欲报答吾皇陛下的浩荡皇恩,便欣然应允,当了朱元璋的首席秘书。据郑晓《皇明名臣记》一书所载,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对宋濂说:“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草莱列侍从,为开国文臣之首,俾世世与国同休,不亦美乎!”意即希望宋濂的儿子、孙子都出来做官。随后,朱元璋就任命宋濂的次子做了中书舍人;任命宋濂的长孙宋慎做了殿廷仪礼司序班。祖孙三代同时在朝为官,的确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宋濂对浩荡皇恩十分感激,告诫子孙说:“上德犹天地也,将何以为报?独有诚敬忠勤,略可以自效万一耳。”然而,正是这浩荡皇恩,后来却成了宋濂一家的灭顶之灾。宋濂退休后,回到老家专心读书著述,打算安享晚年,可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洪武十三年春节期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将丞相胡惟庸处死,随后开始追查“胡党”,结果,宋濂的孙子宋慎因曾与胡惟庸走得太近而被定为“胡党”成员,被处死;次子也被株连而死;宋濂自然也在劫难逃,被押解到南京候审。朱元璋准备处死宋濂,但太子朱标极力求情,马皇后也为宋濂说好话,朱元璋便留了宋濂一命,改为流放四川茂州。那时的宋濂,已经七十多岁了,还要披枷戴锁不停地赶路,受尽了折磨,半路上就死了。试想,如果宋濂当初不再对功名利禄抱有任何留恋之心,谢绝朱元璋的邀请,在龙门山潜心著书,做个幽游林下的世外散人,还会有后来流放至死的下场吗?或者说,当朱元璋任命他的儿孙为官时,他能极力推辞,不让儿孙进入官场,儿孙以后当然也就不会成为“胡党”了。其实,退休后的宋濂,也有所醒悟,他曾说:“末年引疾,实拂圣心,若有意避远,并子孙亦杜仕籍,恐天威一振,全族皆沉。”可惜的是他醒悟得太晚了!
深受皇帝的恩宠,表面上风光得意,其实却暗藏着危险的基因。人生有四大靠不住:春寒、秋暖、老健、君宠。春天本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个时候天突然冷了,这种冷不会长久,因为它违反了季节变化的规律;同理,秋天是万物萧疏的季节,如果突然暖和起来了,这事儿也不靠谱;人生步入老年,身体日渐衰弱是正常现象,如果突然健壮起来,并不是什么好事;这其中最靠不住的,就是君宠,因为皇帝这种政治动物,做什么事都是从自身的政治需要出发的,是以理性代替感情的,而且喜怒无常,正所谓伴君如伴虎也,别看他今天对你恩宠有加,说不准哪天一翻脸,你就要大祸临头了。受恩深处宜知退,只知进、不知退,日后的悲剧也就注定无法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