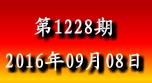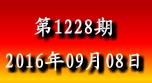我国智库大扫描
我国智库大扫描
□刘一 程姝雯 方澍晨
据统计,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已达2000余家。一般来说,大决策会同时向多个部门、机构征求研究咨询意见,到了真正的起草过程阶段,还会反复权衡,反复征求。
30多年里,中国为政策出台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意见的学者不计其数。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智库如何为决策者提供支持?
“国家队”直接参与政策制定
毫无疑问,在官方智囊机构中,“国研中心”和中国社科院(以下简称“社科院”)是对政策影响最大的机构,甚至直接主导参与政策的制定。“国研中心”专注财政税收的研究员倪红日介绍,中心的课题,有的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直接交办的,有的则是与各部委协作。比如他们参与的“十二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十二五”规划指标体系研究等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课题,而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研究子课题中国碳交易市场机制研究等,则是国家发改委委托的课题。
2013年1月24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发布《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对来自182个国家的6603家智库进行评估。在“全球官方智库排名”中,共有40家智库榜上有名,其中中国6家,“国研中心”排第26名。在2012年的榜单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更是位列亚洲智库第1位。
“参与‘顶层设计’的智囊常常以集体、机构的名义对外发声,放出的口风更注重改革的内容和具体的细节。”法学博士、学者刘峰在博客中写道,“智囊团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宣传研究成果、中央精神;另一方面期待扩大影响、获得民众支持,进而又反馈给‘上面’,进一步达到献计献策和影响政策的功效。”
“写几十万字很容易,但要用2000到2500字把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说清楚,是很难的。有时候一句话就是一个重要观点,可能决策就会据此而定。”倪红日如此谈及官方智库在报告措辞上的重要性。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主任慕海平则在采访时透露,原则上,每篇决策咨询报告的字数不超过3000字,其中送阅件的字数可以更短,可以是1000字,甚至是500字。“必须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慕海平说。
“学院派”出身阵容不俗
2013年10月23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22位知名外企高管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其间,习近平微笑着表示,“你们作为世界知名企业家,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有着深刻见解,我愿意听取你们的真知灼见”“你们的建议是中国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
这群外企高管的身份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海外委员。此前,“学院派”智库从未如此高调浮出水面。经媒体报道,该委员会成员级别甚高,由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担任名誉主席,成员包括61位跨国公司董事长、总裁或CEO;世界知名商学院院长;国内企业家及国内财经界高级官员。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哈佛大学校董会董事吉姆·布雷耶、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阿里巴巴集团执行主席马云、中财办主任刘鹤都是当年加入的“新面孔”。
在过去的14年中,这一“智囊团”频频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而见诸报端的公开信息却少之又少。
2001年,朱镕基卸任经管学院院长时,曾透露过它的“身世”:“1984年,我受刘达同志邀请来做院长。我本来没有学过经济,但对管理特别感兴趣,所以不知高低,一口应承。”由于政务繁忙,经常顾不上学院工作,朱镕基觉得愧对母校,于是“就把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者邀请来,成立了顾问委员会,希望能对经济管理研究院的成长有帮助”。
此后,朱镕基保持每年会见一次顾问委员的习惯。在习近平接见海外委员的当天,朱镕基也出席了此次活动,与委员们交流了1个半小时。其间,他还幽默地问起:为什么委员们看着越来越年轻?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兼全球总裁鲍达民笑答:“因为跟清华的学生在一起。”
鲜为人知的是,像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下属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学院派”机构中,也有不少“国家队”成员,诸如周其仁、樊纲等都是经常出入中南海的经济学家。
民间论坛各显神通递报告
据统计,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已达2000余家。
前述智囊人士称,经过多年的执政探索,中国式决策正在不断变得科学化和民主化。据他介绍,一般来说,大决策会同时向多个部门、机构征求研究咨询意见,到了真正的起草过程,还会反复权衡,反复征求。“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机构的研究成果上报中央已不是什么独家特权。”他称,现在是一个“全民建言”的时代,成果上报渠道的多元化和官方逐渐开明的态度,注定某一家机构的研究成果不可能完全成为政策本身。
2013年2月17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其主题关注的亦是“改革的重点任务和路径”。和高校中的“学院派”类似,这一论坛也非政府组织,尽管一些成员担任了政府职务,且国家信息中心和中国经济信息网在论坛成立初期给予了助力,该论坛一直是由经济学者自发组织的交流平台,成员皆以学者身份参与活动。
刘鹤也是该论坛的学术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曾撰文回忆:“1998年6月,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经济学者之间需要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他提起,他和樊纲在木樨地的一家小快餐店里讨论了这个想法,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于是决定发起“50人论坛”。此后,该论坛的成果通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月报》等渠道上报到相关政策制定和国家管理部门。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概念源自西方“think tank(思想库)”一词,原本就带有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组织色彩。
上世纪90年代,在科技“下海”的浪潮中,一批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开始组建智库,如林毅夫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樊纲的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等。他们利用各自的渠道,也将一些研究成果上传到中央或相关部门负责人手中,丰富了有关部门的参考素材。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国金融40人论坛”等2013年都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在公众看来,智库的划分多种多样,建言的途径也各不相同。不过,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则认为,中国的智库最好不要用民间、官方的方法简单划分,不要在思想库上贴标签。